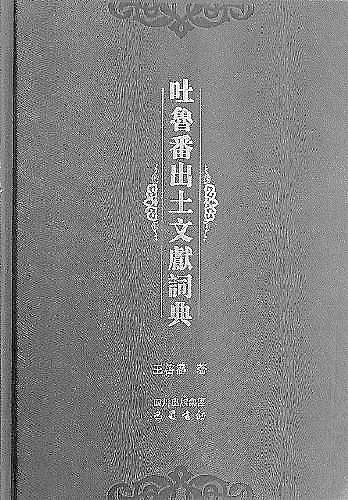由于吐鲁番文献来自千年以前的官府和民间,文书拟定者、抄写者和阅读者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其中的俗字别字数不胜数,加之方言俗语、文言古语、行业术语、体裁套语连篇累牍,从而导致文史领域和词典编纂领域对其误录、误释和误注,郢书燕说,时常发生,而目前敦煌吐鲁番学“似乎有忽视基本工具书的编纂的倾向,而且未能有超出个案研究的鸿篇巨制问世”(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大学出版社),所以,吐鲁番文献亟需有一部基础性、总结性的“词典”类著作问世,以帮助各领域的学者在阅读和使用吐鲁番文献时扫清语言文字障碍。现在,西南民族大学王启涛教授《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以下简称《词典》)终于出版(巴蜀书社2012年6月),该书300万字,历时十年撰成,作者呕心沥血,字斟句酌,对吐鲁番出土文献中7000个词条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和训释。该书一出版,就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该著获得中国语言学最高奖——北京大学第十五届王力语言学奖、第二十八届全国优秀古籍图书一等奖。综观该著,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由语言文字学入文献学,其文献学可信。当下学人对传统文化的使命,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文化整理、文化研究、文化传承,其中,文化整理是基础,怎样进行文化整理呢?清代学者张之洞曾说:“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张之洞所言“小学”就是语言文字学,它是文史研究最基础的一环。由于历史文献产生于遥远的古代,时有古今,地有南北,那时候的语言文字系统已经不易被今人识读,加之传世文献在历代的传写刊刻中有意无意地被改动而失其本真,出土文献又因书写者文化水平的参差不齐以及地下保存环境的各不相同而残缺不全,因此,我们必须首先下一番文字、声韵、训诂功夫,将文献中字、词、句的本义搞清楚。中国古代的学者,特别是清代的乾嘉学派,一直坚守这样的优良传统,直到近现代,王国维、陈寅恪等学术大师都有非常富厚的语言文字学功力,甚至本身就是一流的语言文字学家,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这一传统正受到忽视。《词典》在确立和收录每一个词条时,基本上都是以见到文献原件或原件图版为前提(作者为此十年来一直奔波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地区博物馆以及大英博物馆等海内外吐鲁番文献收藏机构),在前贤时彦的基础上,对吐鲁番出土文献原文进行了重新识读、校勘、录文和考释。《词典》详尽保留了这些考释过程,不少词条完全是一篇精彩的语言文字学专文,这从“匕列、匕例”“马半”“胡禄”条可以看出,所释均可为定论。
二、由文献学入史学,其史学可信。清代文史大家王鸣盛有一段话颇具说服力:“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中国书店出版社)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实现文史互证,《词典》在这一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比如吐鲁番文献中有“羇人”一词,《词典》训释为“羁拘、羁留之人”,《词典》首先提供语言文字学上的证据:《玉篇·网部》:“羇,羁旅也,寄止也。”“羇”同“羁”,《篇海类编·器用类·网部》:“羇,通作羁。”然后从历史学上进行论证:原来,唐击败突厥以后,原先逃往突厥或被突厥掳掠的汉人返回唐朝,道经高昌,被麴文泰扣留,并进行奴役。《词典》引用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三十《蕃夷》“讨伐”所收《讨高昌王麴文泰诏》以及《新唐书》卷二二一上《西域》上“高昌”等史料为证,把这一史实讲得一清二楚。
三、由考据学入词典学,其词典学可信。陈寅恪先生言:“夫考证之业,譬诸积薪,后来者居上,自无膠守所见,一成不变之理。寅恪数年以来关于此问题先后所见亦有不同,按之前作二文,即已可知。但必发见确实之证据,然后始能改易其主张,不敢固执,亦不敢轻改,惟偏蔽之务去,真理之是从。”(《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学术研究,贵在不断吸收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而又有自己的发明。《词典》把百年来前贤时彦在吐鲁番文献研究方面的宝贵成就进行忠实介绍,带有浓郁的“集解集释”性质,具有“集大成”的学术气象。
但是,这样做会遇到一个挑战,在罗列前贤时彦的见解时,作为一部专业词典,还应该告诉大家:哪一家的观点是对的或接近对的?为什么是对的?这就需要词典作者具有淹博、识断、精审三种学术修养,当代学者钱钟书在评价钱仲联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时也曾经指出:“集释真不容易写,你不但要伺候韩愈本人,还得一一对付那些笺注家、批点家、评论家、考订家,他们给你许多帮助,可是也添你不少麻烦。他们本来各归各的个体活动,现在聚集一起,貌合心离,七张八嘴,你有责任去调停他们的争执,折中他们的分歧,综括他们的智慧或者驳斥他们的错误——终得像韩愈所谓‘分’个‘白黑’。”(引自钱钟书著、舒展选编《钱钟书论学文选》第六卷,花城出版社)值得肯定的是,《词典》对于前贤时彦的研究并不只是罗列和介绍,而是能够表态和定夺,并把自己的考证过程全部展示在《词典》中,从而使《词典》带有浓郁的考据性质。今兹举一例: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反复出现“手抓、手抓囊、脚抓囊、脚爪囊、手爪囊、手脚爪囊、指抓囊”,究竟何义?或以为当为御寒之物,或以为乃装随葬手指甲、脚趾甲的小包,《词典》第933页指出以后者为是,并补《新唐书》卷二十《礼乐十》之用例以证之,同时还指出“直到今天,在甘肃武威等地,依然有此丧葬习俗”。又比如:吐鲁番文书有“队陪”一词,究竟是何义?直到今天还在争论,《词典》第284—285页认为“队陪”实即队形(行军作战时每一个士兵所站的具体位置和职责,也就是谁跟着谁,谁的左右前后是谁),令人心服口服。
曾忆老一辈敦煌学家蒋礼鸿先生之《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被誉为研究中国通俗小说和敦煌文献的“指路明灯”,享誉海内外,迄今已经再版五次,我们希望《词典》与之形成双璧,不断增补和再版,共同促进敦煌吐鲁番学的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