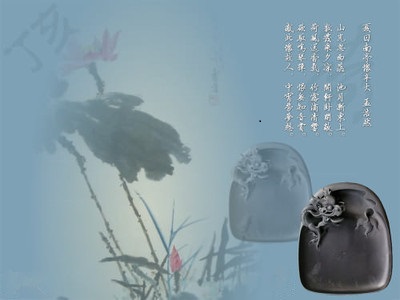
【图语:《夏日南亭怀辛大》,体裁为五言古诗,唐代诗人孟浩然所作】
国家社会的基础是文化教育,只教知识技术还好办,但文化教育的瓶颈在人性的顽固弱点,这也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根本瓶颈。古今中外,人们每每不满现状,不断地探索政治、经济、社会的理想道路,不断地尝试革故鼎新,可是不久就会发现,一切又开始了异化。于是,这种革故鼎新的冲动,在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着,永无休止。很多伟大的社会理想,通过努力好像近在眼前了,可以不久之后,好像又远在天边了。可以说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但也可以说是一种怪圈的轮回。这个轮回的背后,是人们不断探索世界改造世界的同时,却永远要面对无常,面对极难改造的自己。表面的改造是有的,深层的就是“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了。越是改造不了自己,就越是寄托于诉诸于外在世界的改变。这是一种悖论的轮回,思维的陷阱。即便再好的制度,面对人性的痼疾,也往往捉襟见肘,常感无奈。
所以说,改造世界首先应从改造自己入手。《大学》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本末因果的关系。但现实中,人们是本末颠倒的,只希望家齐、国治、天下平,却不愿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都想改变别人,却不愿改变自己。只想品尝果实,却不愿辛勤耕耘。所以,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理想,如何去实现呢?
据说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有一块墓碑,写着著名的一段话,大意是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漫无边际,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一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以后,我发现我不能够改变我的国家,我最后的愿望仅仅是改变我的家庭,然而,这似乎也不可能……现在,我已经躺在床上,就在生命将要完结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就首先改变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重要的事情。就在我为国家服务的时候,我或许能因为某些意想不到的行为,改变这个世界……”这段话,和上面讲的《大学》里那段话是一个方向,但《大学》提供的,是一套更为系统完整且理性的,可操作可实行的因果路线图。(马宏达,2014年3月2日上海恒南书院,南怀瑾老师诞辰纪念讲座)












